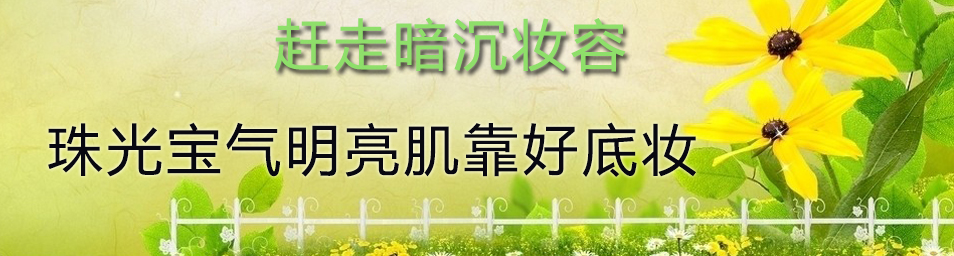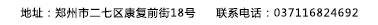|
想象一下,你和两个朋友约好见面。住的更远的你,为了准时赴约,午饭也没吃,就早早出发了。 没想到,到了约定地点,你等了半小时,另外两个朋友才来。一问,俩人已经吃过饭了,此刻的你,又饿又生气,你会怎么做? 是假装无事发生,还是如实表达心情?更深层的问题是: 你在自己的感受和照顾别人之间,如何选择? 01害怕被讨厌,不敢活出自己前两天,朋友春雪加班到晚上9点,叫了车回家。上车没多久,司机就热情搭讪:“小姑娘,这个点儿才下班啊?” “嗯,是啊”春雪回答道。 “现在的年轻人,真不容易啊!” “嗯,是挺累的” “哎,现在钱真的不好挣啊,你是不知道,我早上今天碰见一个客人,绝了,给我打了个差评…” 春雪有点尴尬,本来累了一天,想听听音乐,放松放松,但又不敢不接话,只能顺着司机的话说: “为什么啊” 司机说:“他坐上车,就开始催,我总不能闯红灯吧,但他还是一个劲儿的催,最后他上班迟到了,就为这,给我一个差评…” 此刻,春雪有点无奈,花了钱,还要听对方抱怨,表面上,却不敢让话掉地上,应和道:“嗯,是挺过分的”。 “是啊,这人不会早点出门吗,催我有什么用?这还不是最恶心的,你是没见,我那天…” 司机打开了话匣子,春雪只能忍着不适,“嗯嗯,哦哦”的陪了一路。 图片来源:pexel明明很烦,却不得不勉强作陪。 这样的场景,生活中有很多: 逛街时,明明你只是想试穿一件毛衣,却被导购围着不放: “这衣服太衬你肤色了” “你这么白,穿我们家另一款大衣,肯定好看,我拿来给你试试” 你明明想逃跑,表面上,却在尴尬假笑,无奈地接过对方递过来的大衣。 类似的场景还有: 你一个人坐火车,拿行李,找座位,折腾半天,好不容易入座。一个女生拍拍你肩膀:“你好,可以和我换个位置吗,我朋友在旁边。” 这时,坐在你旁边的女生投来恳切的目光。正当你犹豫时,对面座位上的男生开口了“你就和她换下嘛,我们都一起的” 本想拒绝的你,话到嘴边,又憋回去了,还是忍着疲累的身体,换了座位。 为什么,在自己的需求和别人的需求之间,你容易牺牲自己? 因为,只顾自己是会被讨厌的。 明明很烦出租车司机,却不敢表达,因为怕一表达,就会被讨厌。 明明很烦导购,却不敢拒绝,因为怕一拒绝,会被嫌弃。 明明不想动弹,却被迫换座,因为怕不换座,会被旁边的人讨厌一路。 这一种很正常的情绪。但这种情绪,却会让你活的唯唯诺诺,低眉顺眼,而你真实的生命能量,被严重压抑了。 图片来源:pexel 02问题的核心在“小我”为什么,我们都在竭力避免被讨厌? 因为,被讨厌,会有后果。 朋友小A,念书时,曾被一个女生讨厌。走在路上,她主动打招呼,对方直接忽视。来她的宿舍分家乡特产,她所有的室友都有,唯独略过了她。 更过分的是,有一阵子,她开始拉拢小A的闺蜜,试图排挤小A。提起那段经历,小A又愤怒又痛苦。 被人讨厌,确实会让人很难受。知乎上,有一个提问:“被人讨厌是怎样的体验?” 有人回答: “是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” “心像被钉子扎了一样难受”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痛苦? 在阿德勒的《被讨厌的勇气》一书中,有这么一段: 哲人问:“被别人讨厌时,你会有什么感觉呢?” 青年回答:“那当然是很痛苦啊,会非常自责并耿耿于怀地冥思苦想:为什么会招人讨厌、自己的言行哪里不对、以后该如何改进待人接物的方式等。” 发现没,当我们被讨厌时,第一反应往往是:“会不会是我哪里错了?”之后,这个问题又会上升到:“会不会是我不好”。 我一个发小,经常和我吐槽同事。 “我那天看她加班,好心帮她做了几张PPT” “可她倒好,事情没做好,甩锅到我头上...” “我平时对她多好呀,我妈给我寄的特产,都给她带一份,她呢,不帮我也就算了,居然还甩锅给我” 每次吐槽,她会反复强调,自己的“清白”,放大对方的“错误”。我能明显感到,她在向我证明:“她是对的,对方是错的。” 似乎只有证明了这一点,我才能接纳她。而我很想告诉她:“即便你错了,我也会接纳你” 图片来源:pexel错误,是人的一部分,但不是人本身,即使你错了,并不等于,你就是不好的。 这里的“对错”,是思维范畴的,而“你”则是一种存在。“思维”不是你,但很多人会把思维与人画等号。 这就像拿葡萄藤上的一根枝蔓,来定义整个葡萄藤。心理作家EckhartTolle把这个叫做“小我”。 EckhartTolle表示,“小我”不是真正的自我,真正的我是一种深刻的临在,是一个内在观察的,无评判的心灵之眼。 也就是说,我们的思维不是我们本身,而那个观察思维的存在才是我们本身。 当我们陷入“小我”时,就远离了真正的我: “小我”说:“他讨厌你,一定是你哪里不对,你不够好......” 当你相信“小我”的声音时,你会发现,他人的否定,否定了你的存在。于是,你只能唯唯诺诺,不去得罪别人。 而真正的你,严重被压抑了。 相反地,当你意识到,思维不是你。就算他人讨厌你,就算你错了,也无法否定你的存在,你就能拥有被讨厌的勇气,真正的活出自己。 0害怕背后是“异类思维”刚刚说到,我们往往害怕被讨厌,不敢拒绝别人。与此同时,还有一种怕被讨厌,是害怕被看作“异类”,因此做事小心翼翼。 我的朋友小N,就是这样。上班时,只敢躲在卫生间偷偷补妆。 一旦听到脚步声,会赶紧收起口红,粉饼。因为怕遇见熟人,怕被评判为虚荣,肤浅。 成年人补妆,再正常不过的事,在小N眼里,却会成为被讨厌的理由。 图片来源:pexel为什么会这样? 原来,小N从小就是典型的“乖孩子”。上学时,总是齐耳短发,黑框眼镜,素面朝天。 看到学校爱美的女孩子:薄薄的裸色粉底,不灵不灵的唇膏,蓬松的丸子头,人堆里鹤立鸡群。 小N就会想:成天就知道涂脂抹粉,太虚荣了。在她眼里,这样的女生就是“异类”。 这种心态,就像一面双面镜:她在评判别人时,自己也被限制:自己会这么看别人,理所当然,别人也会这么看她。 所以,她总是竭力隐藏这一面,生怕被别人看见。 很神奇的是,害怕被别人当“异类”,可能潜藏着“异类思维”,即:有的人是对的,有的人是错的,而这样的思维方式,本质上是一个误区。 因为,它的前提是:认为“思维”就是“我”,这个“思维我”,也是上文提到的“小我”。 ‘小我’的特征是二元对立:有对,必然有错。 即: 有深刻的,就有肤浅的。 有聪明的,就有愚蠢的。 有涵养的,就有没素质的。 若我的立场是正确的,那么立场相反的你,必然是错误的。 “小我”还有另一个特征,即自恋。 我们更容易认可自己的特质,而贬低相反特质。这就导致,我们容易看不惯特质相反的人。 心理作家EckhartTolle说了这么一段话: “如果思维被正确利用的话,它是一个超强的工具,但如果利用不当,它的危害相当大,准确的说,不是你利用思维,而是它在利用你。” 当我们跳脱出这场文字游戏,回到存在本身时。我们会发现,世界是多维的,不是二元的。跳脱出“对错”,还有第三种可能: 我是对的,你也是对的 我是合理的,你也是合理的 不被“小我”限制最关键的一步是:从对思维的认同中摆脱出来。 图片来源:pexel 04如何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如果你被他人讨厌,感到很痛苦。 如果你惧怕他人眼光,不敢活出自己。 怎么走出这个困境呢? EckhartTolle指出,唯有把“思维”与“我”分开,才是改变的开始。当我们意识到,“思维”与“我”,是两码事,会发生什么呢? 你会发现,他人的讨厌,也许代表“你错了”,但永远不代表“你不好”。因为思维的对错,无法定义存在本身。 如此一来,他人的讨厌,无法构成存在的威胁,这时候,你会发现,他人的讨厌,是如此没有杀伤力。 同时,当你惧怕成为异类,也是把“思维”与“我”混为一谈。 当你不再认同“思维”,跳出“对”与“错”的二元世界,你就会发现,哪怕与我们立场完全相反的他人,也是对的。 而你也不再惧怕,被这座双面镜限制。这时,你会具备成为“异类”的勇气。 以上两种情况,都需要我们摆脱对“小我”的认同。 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: 练习“真正的我”状态 正如心理作家EckhartTolle所说,真正的“我”是更深刻的临在,是一个观察,无评判的心灵之眼。 因此,要摆脱对思维的认同,就要更多练习这个“真正的我”的状态。 (1)倾听思维 心理作家EckhartTolle指出:倾听大脑中的声音,你会发现:有一个观察的临在,它可以倾听你的思维。 当你意识到你的思维不是真相,你就会停止认同你的思维,而这是摆脱“小我”的第一步。 图片来源:pexel(2)自由书写 上文提到倾听思维,可能会有点抽象。这里可以把情绪当线索,来观察你的思维。 例如,今天心情有点down,找一个地方,写下来,问问自己为什么,倾听背后的思维。 反复练习,你会发现,很多想法只是一种想法,仅此而已。 ()活在当下 真正的自我,是一个观察性自我,它不仅在观察内在,也在观察外在。我们常常不允许,这个观察外在的“我”出现。 例如,昨天我在花圃旁散步,我的头脑却在世界大战: 待会儿吃什么? 上周去了哪里 记得回家取快递 各种信息,在我的头脑里乱窜。我看不到旁边的花圃,是什么颜色,有没有新发的枝芽。 因为,一旦我的大脑停下来,我会很不习惯,我会觉得有点无聊。而为了对抗“无聊”,我的头脑在飞速运转。 实质上,“无聊”只是我的想法,而我认同了这个想法,于是我的“小我”又开始运转。 这时候,可以观察到“我有点无聊”这个想法,然后把意识温柔的,不评判的拉回当下。 而此刻的丰盈,就是生命本身。 回归存在本身,你会发现,你本是勇敢与自由的。 图片来源:pexel 为了感谢大家的
|